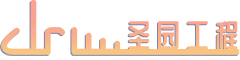樓梯假山-被遺忘的一隅,如今卻成了精魂所在。
這假山,原是樓梯下被遺忘的一隅,如今卻成了整座屋子的精魂所在。它并非巍然矗立,而是謙卑地偎在墻角,仿佛是從大地深處自然生長(zhǎng)出來的一片微縮的山水。嶙峋的石體堆疊出奇妙的韻律,瘦、透、皺、漏,該有的品格一樣不少。光線從樓梯的間隙篩落下來,便在這石上演繹出無窮的變化——晨光是淡金的輕撫,午后的光是凝脂般的流淌,待到暮色四合,一縷溫柔的余暉便恰好停在最高處的那處凹陷里,像一只溫順的鳥兒,斂翅歇息。

我的目光日日撫過這片微縮的河山,便也漸漸讀懂了它的語言。那聳起的,是孤峭的峰;那深陷的,是幽邃的谷;石上蜿蜒的白色紋路,便是千百年前凝固的流水痕跡了。更有那青苔,是時(shí)間繡上去的綠絲絨,茸茸地、懇切地生長(zhǎng)著,尤其在雨后,那綠意幾乎要滴落下來,洇濕周遭的空氣。旁邊伴著一株小小的南天竹,細(xì)碎的葉子在石畔疏疏地?fù)u著,像一個(gè)清雅的夢(mèng)。
這方寸之間的天地,竟比窗外的整座城市更要令我安心。它有一種靜穆的熱鬧。我仿佛能聽見,光與影在其間行走的簌簌聲,水汽在青苔上凝結(jié)的細(xì)微聲響,以及那凝固了千萬年的石頭,在無人注視的深夜,發(fā)出的一聲滿足的嘆息。它以自己的靜,涵養(yǎng)了一切動(dòng)的生機(jī)。于是,捧一本書在此靜坐,書頁上的字句,似乎也染了石頭的沉靜與青苔的鮮活;從外頭帶回來的滿身塵囂,只消在此站上一會(huì)兒,便不知不覺地被那石頭的清涼與綠意的溫潤(rùn)洗滌凈盡了。

我不禁想起古人的園子,那不僅是土木,更是精神的棲居。白居易的廬山草堂,有“片石孤峰窺得我”的相看兩不厭;米芾見奇石則整衣冠而拜,那不是癡頑,而是對(duì)造化之功最誠致的禮敬。我這樓梯下的一方假山,雖無古人之規(guī)模,所得的神韻卻是一般的。它讓我在汲汲的奔走中,得以“不下堂筵,坐窮泉壑”。它是我案頭的山水,是我心間的林泉,是這凡俗生活里,一個(gè)觸手可及的、清亮的夢(mèng)。
這假山,靜靜地立在那里,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。它從不言語,卻告訴了我一切:關(guān)于永恒與剎那,關(guān)于喧囂與寧靜,關(guān)于遠(yuǎn)方與眼前。它將一座真山的魂魄,邀至了我的廳堂;又將一片自然的清供,安放在了我的心間。每日我上下樓梯,腳步經(jīng)過它,目光便與它有一次短暫的交接,那仿佛是一種默契的問候,一次精神的洗禮。這小小的假山,竟成了我安放自然的神龕,更是我寄托情懷的所在。